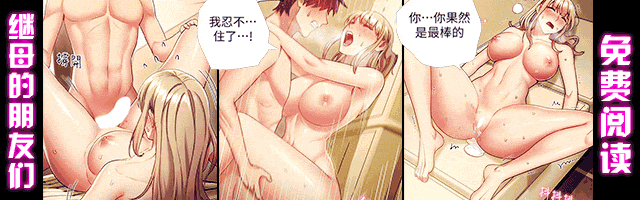「我梦到一轮红日当空照,妾身正行走间,却听人大喊:『我来也!』我回顾不见人迹,乃仓皇逃跑,又听喊声自天上来:『我来也!』却不知是何妖怪,壮胆抬头望,只见红日遂坠,妾身正惊慌间,却被老爷你给拍醒了。」
王老倌匆匆执其手,追问:「果真如此?」
蛾娘本欲挣脱,却不便,遂嘟哝道:「梦中所指,原当不得真的!」又觉腰间被那大物顶着,遂动也不动。
王老倌以横额望天而谢曰:「前日方士说我子孙入仕做官,我却半信半疑,今自蛾娘得此好势。我便信了。」
蛾娘不甚明白,拿眼询他。
老倌极喜,拥蛾娘道:「古时赵洪恩妻王氏忽梦日落怀中,遂生出个大宋皇帝来,今爱妾梦红阳坠落怀中,不是正应了子孙临官入仕之说?小娘,快和老夫行房,播个龙胎虎种,让我王家也扬名立万一回。」老倌心里急切,伸手欲解蛾娘衣衫。
蛾娘听他说得有头有尾,并不疑他,任其解衣松带,索性将胸衣下衣全数掠尽,裸体相呈。老倌见她全身红润,肌肤结实细腻,滑如羊脂,每一处都令人爱煞,一时不知从何入手?
蛾娘侧卧於床,以肘撑起上半身,因扭曲着身子,那双乳变得一小一大,皆挺拔细嫩,不似官宦小姐之物苍白,却比她们之物有韵。老倌双手摩抚大乳,吮其乌红乳头,乳头状若大颗葡萄,吸入微觉涩苦,大概农家女勤於劳作,积存若许汗垢,也是应当的。
老倌吮了片刻,见蛾娘亦大声喘息,乃知其亦知味也,遂殷勤作法,用手抚其阴户,但觉紧紧扎扎只容一指可入,老倌并不着急,换其阴唇,抠其皮肉,捋其毛发,摩其「小阴茎」,一只魔手交换多端,只不离那肥沃之地。
忽然,老倌觉得蛾娘阴户朝前一挺,俟他再摸,乃鼓凸而出,状若紧紧蹦蹦热热滚烫馒头,只中间缝儿更见狭小,若那崇山峻岭之间,唯有一条羊肠小道可入,王老倌出小指轻轻摁入,却被一物阻住,再摁,乃觉反弹力道甚大,奇乐:「小娘若非石女乎?」
蛾娘诉曰:「怎麽?平时俱撒得出尿来,想必是通了的!」
老倌大笑:「撒尿之窍和交合之窍不同也,两窍非一窍也。小娘平生可否排泄秽物?」
蛾娘被他逗得浑身酸胀,乃从实道来:「半年前始排尔!乌血黑块,怪吓人的。」
老倌却了心头疑虑,遂问道:「汝窍甚小,我物甚大,我不忍强破之,恐尔有事。」
蛾娘阴户又是一挺,只觉户内淫水鼓荡,外庭溢鼓,略比刚才高出几分,那裂缝也竟然弥平,老倌手指也自脱出。他想起玉娘奇物,不知蛾娘又是什麽光景,乃以手猛撬「小阴茎」。
蛾娘已如待发之箭,急语:「老爷,而今恐怕不做不行了,奴家里里外外俱痒,须你想个法儿解解。」
老倌见她全身桃红,唯那阴户又高又鼓,比起平常态,此时宛若埋了白白嫩嫩大地瓜在户外,老倌提起阳物,瞄准那细缝儿往里塞,却水到渠成,门庭可进,蛾娘唯觉大龟头触及时,心里惊,皮肉酥,便知它才是解痛的主儿,遂呼道:「老爷,放那大鸟飞过去?!奴家里面有若许小鱼喂它!」
老倌听她话语新奇,遂问:「你怎知道?」
蛾娘呻吟而语:「细水潺潺,幽潭深深,不长鱼又长甚?再说这时痒得紧,一定是那鱼儿摆尾甩头弄的。」
老倌单说闲话,但阳物却未闲了,几番冲击结果,俱被白皮铁门儿挡住,一面怒气勃勃,一面重振雄风,只见老倌猛吸一口气,手持大阳物,望蛾娘阴户凭空砸下,宛若石匠狂夯那青石条。只见白皮门儿「咚」一声响,弹了几弹,阳物便歪至一边,那门儿却丝毫未损,摧香又告失败。
老倌又破又打,均无建树,蛾娘憋得全身香汗涔涔,青丝亦胶结成一条辔,凶急了,便道:「早知此门难开,奴家该从娘家带把锥子来。」
且说老倌弄耸多时,依然无法撬开蛾娘春宫大门。老倌思忖:「她既非石女,只要她现存洞儿撬,还怕揭不开这软皮儿。」
老倌遂将锦被叠成方墩,把蛾娘横担其上,让她两头着床,胯部上掀,蹲下,将指刮除膜儿上黏物,细细审视起来。找不见洞儿,老倌又问:「小娘子,果真泄了?」
「泄了,泄了,泄了几趟了!」蛾娘答非所问。她忍耐不住,被老爷弄得泄了三次阴精,只排不泄,故那阴户越鼓越涨,把那一白皮儿绷得甚紧,洞儿也抹没了,她听老爷问她,便如实报来。
老倌眼见窗外天已微明,隐有雄鸡啼叫,估摸已至寅时,再不设法,恐今晚不能破之,虽无大碍,却甚难为情。
俗话说,急中生巧智,老倌沉思片刻,果断伏於蛾娘阴户,鼓凸嘴唇呈横状,先哈出肺里气息,似阴茎投於阴户,大力吮之,「嗖嗖」之声不绝於耳,彷佛自那绸绢上抽丝,蛾娘户内淫水呈线状从那洞儿射出,老倌悉数咽之。
约莫一袋烟工夫,那鼓鼓凸凸之物便减低几分,最令王老倌欢庆的是,他终於寻着那针尖般大小洞儿,户内淫水泄也,白膜此亦松弛了许多,老倌乘势冲锋,他着帕儿扶得阳物更加强硬,一手撑蛾娘外阴扇出那一片,一手持自家阳物,瞄那细肉洞儿猛捣,一气捣了五十余下,犹似村中老农捣米,一棒比一棒卖力,捣得蛾娘欢唱连天:「亲亲老爷,亲亲老爷,亲亲男人,亲答答,肏得奴家快没魂了!」
她喊得紧,老倌亦捣得凶,因他五内慾火腾腾燎烧,阳物亦涨得筋络鼓凸,宛若一支乌金的锤。
且说老倌捣了又捣,只见那白膜儿陷进若许,整个龟头亦陷没了,他以为大功告成,谁知阳物甫一松劲,那膜儿又弹了回来,内中洞儿确比初时大了许多,淫淫春水箭簇般任处喷射,谁知蛾娘又泄了几回?只见她白眼儿上翻,口里气息喘喘,只是户内骚痒劲儿解除不了,令她难受不已。
老倌暂歇一歇,以手指套入肉洞,本想弯指作勾撕破了它,却怕蛾娘受不了痛,更兼自已亦没了男人体面,故只撑了几撑便松了,虽然收效不大,但有进展,亦不气馁。
蛾娘以为老爷放弃不干,遂急道:「老爷,奴家这里面恐怕被虫子吃烂了,乾脆,找把刀来割开算了。」
老倌一笑,遂记起余娘拿刀划缝的趣事,心头频添若许英雄气,他令蛾娘自家把手掰开阴户,他则後退数步,双手平端阳物,瞄那膜儿奔杀进去。
只听得「噗哧」一声响,老倌阳物终於攻城拔寨,将那膜儿撞成碎屑,蛾娘「啊呦」一声,痛得花容失色,全身乱抖,老倌亦知旗开得胜之猛将,哪有怜惜之意,只管大力冲刺,风车般劈了五百余下,砍得蛾娘渐渐没了知觉,老倌急火急扯,不知自家正和黄花闺女走头遭,却如正和余娘交锋。
又提了三百余下,蛾娘回复知觉,只觉得自出那环儿捏着扯着核桃般一个芋头,芋头冲撞往返,挠着了痒处,擦着了骚处,却又添了若许痒处和骚处,只恨他上面不长倒勾儿,若那勾儿拉拉扯扯,岂不更加快活!
蛾娘更觉畅快,却觉穴口处有种火烧火灼的辣味儿,但到底快活胜过苦头,遂芳心大慰,任老倌狠提深肏。
老倌又觉出另一番妙味,因蛾娘阴户穴口甚紧,捏得他阳物酥酸麻痒,肏时,龟头涨大,抽时,龟头肿胀,而内里却甚滑顺,亦不太紧,只觉得柔柔嫩嫩的肉儿亲亲热热挤挨着阳物,它进,它们则闪,它退,它们则跟,人间之乐,此乐最乐!
巧的是,蛾娘阴户亦不太深,老倌阳物下下俱抵着实在处,及至後来,老倌不似初时那般风急了,全根挺入之後,略顿一顿,左右挫一挫,只因这一挫,却挫得蛾娘飘飘欲仙,要死要活,老倌见她受活,便下下若此,直弄耸得蛾娘喊爷叫娘,一声高於一声,竟然盖得雄鸡亦凝耳驻听不再啼叫。
有诗为证:
人间愁苦多,唯有行房乐。
肏得妇唤爷,抵得爷叫娘。
爷娘亦无空,齐齐喊祖宗。
且说王老倌奋战多时方肏得蛾娘快活,前後约抽了千余二百抽,老倌便汪洋大泄,蛾娘随之亦泄,她竟不知今霄泄几番了。王老倌记挂子孙入仕为官一事,遂伏於蛾娘身上,不取阳物出来,蛾娘阴户颈口确实狭小,连老儿萎缩之物亦含得紧紧密密,了无缝隙。
老倌觉得时间不短,遂抽自家阳物,竟然将那疲软之物拉成一根胡萝?,老倌伺倒退一步,才堪堪扯拖。立即,蛾娘阴户紧闭,虽然比初时少了一层膜儿,却瞧不出那肉洞地,只是老倌用力太猛,竟然将外阴弄得肿了起来,红红亮亮,宛似拿红油浇得东坡肘子。
是日午时,余娘、玉娘、蛾娘、蝶娘先後自厢房中出来,行走时俱是一拐一拐,皱着眉儿,裂着嘴儿,吸着气儿。玉娘、蛾娘、蝶娘处子初破,伤了皮肉,当在情理之中,缘何旧妇余娘亦是这般狼狈?想她历人万千,老倌阳物并非天下至大,况只弄她一回,只因临时替代物老黄瓜个儿太大,余娘极贪吃,不小心伤了内里嫩肉,豁否?不得而知。
如此甚好,大家均无闲话,只蛾娘伤得重些,一双玉腿被迫扭个外八字,金儿、银儿窃窃直笑,余娘笑谓:「两个小蹄子,哪天让老爷也收了。」金儿、银儿却道:「收就收罢!」为何她俩不怕痛?只因她俩见昨日三个少女无甚笑颜,只一夜光景,虽俱成了瘸腿,却眼角儿含情,眉梢儿带笑,想是心里快活之极,故他俩亦欲试试。
且说王定绾一觉醒来,却不见蛾娘身影,见自家衣衫齐整放於枕边,便心道蛾娘体己。穿戴完毕,至各夫人厢房探望,均无人影,抬首望天,却见天上挂着两个太阳,此乃甚麽缘故?只因他─夜连战四人,元阳大泄,故神智昏昏,自古只有一个太阳,他却看出了两个太阳。老倌只觉步伐沉重,如灌沉铅,他却不以为然:「累极而已,将养一日半宿,便无妨。」
他蹒跚行至客厅,却听余娘正宣谕家法:「我虽是家主母,尔等亦是拜堂夫人,从今往後,我等四人共侍老爷,家用银两俱目均等,日後去买三个丫鬟回来,你仨各领一个,金儿、银儿依旧。老爷年迈,尔等乃少年之人,贪玩嗜睡,我操持家务,夜夜难以入眠。」
老倌越听越糊涂,不知余娘下文。他从窗外望那三个小妇人,只见个个水灵灵,粉嘟嘟,余娘和她仨一比,顿时见得老了,老倌心里乐呵呵:「而今夜夜有新人,真个销魂十分。」
他正想得人迷,却听余娘又说道:「说了许多,想必尔等亦明?,具体说来,每旬首尾,老爷入我房,剩下几日,尔等每人两日,尚余两日,一日将养,一日机动。至於你仨如何轮转,各视详情商定,从今以後,吾四人和和睦睦,共理家政。」玉娘、蛾娘、蝶娘诺诺应承。
老倌站於窗外惋惜,他想:「你等俱是我的,我想肏谁便肏谁,还讲什麽次序?」但他素来不敢违拗余娘,只得默默入内坐了。一同吃饭,余娘、玉娘、蛾娘、蝶娘俱夹块肉儿送他碗里,他只得一并吃了,唯恐剩了谁的惹了她呕气。偏偏余娘又挨一块肉他碗里,甜滋滋说道:「老爷昨晚劳苦功高,今晚该将养将养,奴家辅枕以待!」
至此,众女并老倌才明白,所诏「将养」,不过巧立名目让家主母多肏一晚罢了。
是晚,老倌於亲娘房中将养,前後共肏送余娘三千余下,费了三个时辰,翌日晨,他又看见两个太阳挂天上。次晚宿於玉娘房中,只肏她几百余抽,玉娘便说免战,老倌不舍,又肏二百多下,泄了才罢。再次晚宿於蝶娘房中,蝶娘玩个倒浇蜡,虽肏了二千余下,老倌却不嫌累,最後宿於蛾娘房中。蛾娘来个後坐式,仅肏六百余下,老倌便大泄如注。蛾娘本要和他再肏,却见老书困乏至极,便由他睡了。
次日,余娘谓众人道:「今日老爷入我房,此曰机动。」
众女皆有怒气,然不敢发,老倌亦觉无奈,只得机动入余娘房中。余娘全身喷香,酸酸道:「老爷娶了新妇,对我冷淡多了,娘家有甚过错,望君自好或是。」老倌知她意,只得着「起阳帕」扶立阳物,勉强肏她三、五百下泄完便睡,余娘却未吃饱,又独个儿吮吸阳物,施千般手段,玩耍两个时辰方罢。
有诗为证:
首尾入我房,接着要将养;
中间还机动,郎君别打诳。
尔等小妇人,肏你便不错;
夜夜有人肏,痴心又妄想。
且说老倌轮半年不到,便折磨得瘦骨伶仃,而今他看天上已不只是两个太阳了,似若满天都是太阳,还金光灿灿的。欲知老倌性命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